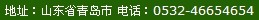|
黄全德 黄全德已经89岁了。 十二三岁起,他就撑着筏子在漓江上打渔。近八十年的漓江岁月:家从江上搬到岸上,从《印象刘三姐》中的孤舟蓑笠翁,到十年前漓江的渔翁拍摄。 一缕白髯的黄全德操着夹杂方言字音的普通话,撑上一张旧竹排,排上拴两只鱼鹰,箩筐里一张老网,为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客人留下一张张经典照片。只是,在国外摄影师为他印制的名片上,他成了“黄金德”;在他颇喜欢的一张《渔翁》照片里,烟波缥缈中独钓的他成了“黄船德”。 他的腰上系着一个发黄的小腰包,里面是“工作”装备:手机店老板送的老人机;几张他看不懂的外文名片;一小撮用红纸裹着的十元、五十元额的钱;一些日常药品。 腰背驼下去,皱纹越来越重,他看着一旁调皮的孙儿,声音却依然有力,“还要做。” 文、图、视频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杨逸男 黄全德住在桂林市阳朔县兴坪镇渔业队,漓江绕村而过,这里的人多以开船、打渔为生。十五年前,黄全德的弟弟黄月创做起渔翁摄影,出现在客人的镜头中。退出《印象刘三姐》团队后,黄全德也加入。他是漓江上最老的渔翁。 镇上的居民都知道这兄弟俩。一打听却不见人,孙儿也不知道爷爷泊在何处。守候至下午三时,黄全德才身挂薄雨衣撑筏子回家。聊不多时,他又赶到岸边盯防戏水的小孩捣乱。 休息半小时又匆匆下水 漓江时晴时雨,黄全德撑着筏子在江上半日,汗水浸透衣衫还没干,雨水又来打湿。回到家,他没有换衫,就挪张矮木凳坐在柴房里聊起来。面对镜头,他一点都不陌生。 今天他挣了块,从腰包里翻出红纸包。“都想照二十元人民币的图像,(我)五块十块都收。”他的包里却少有二十元一张的。 外国游客和摄影师有时会给一两百元,但“今天在拍穿红衣服的。”摄影师最喜欢渔翁日出时分撒网的镜头,“我们力气小,那些年轻的撒得高。”知道他的摄影师常找他约拍,但三点回到家,他的电话还没有响过。镇上手机店送的老人机,他只会用来听电话。 聊不到半小时,黄全德干咳了几声,咽喉有些疼痛。他弓着背,站起来去堂屋找水喝,又从腰包中掏出一个小塑料袋放桌上,里面有两瓶十滴水(祛暑剂)。他不知道如何扭开,让坐在桌旁靠椅上的老伴拿剪刀来,记者忙解释着替他拧开盖。桌上的杂物盒里,他翻出一个白色纸包裹着的药粉,小心抖落在勺中,然后把十滴水一点点挤出倒满,一口喂下去,再就着温开水稀释咽下。 “很清凉,舒服。这个也拧了吧。”两勺下去,他躺着休息一会。这些小病小恙,八十九岁的黄全德都自己解决。女儿前天回家照顾行动不便的母亲,正在煮饭,也顾不上老父亲。 “他的身体算好的了。”女儿说。下雨天穿雨衣,再大点就穿蓑衣,但黄全德还是时常一身湿透。这几年,他的腿脚不如以前有力气了,发痒需吃中药,好在没有落下风湿疾病。 休息不到半小时,担心竹排被戏水的小孩折腾坏,黄全德又匆匆下水,守在竹排上。 本色出演《印象刘三姐》 离兴坪码头不远,有好几个摄影协会挂牌的创作基地。他们的主要拍摄对象就是漓江上撑筏的老人。 最初,张艺谋通过村干部介绍找到打渔的黄全德,邀请他本色出演《印象刘三姐》。加入渔翁拍摄后,找他约拍的人也常常要村里人指引到他家。去年,他把名字和电话贴在墙上,打电话的人有来自“英国、德国、俄罗斯、韩国”这些他不太知道的地方。 为了照起来“好看”,黄全德总是尽量满足客人的要求。他的白胡子留了五六年,以前会刮掉,现在特意留起来。 有一次,一位摄影师想配合江上的日照,递给黄全德一根烟斗和烟袋,让他吸上。这是他第一次烧烟,时不时呛上几声,但还是默默地配合。哪知回到家后,烟气涌上胸口,半夜想吐吐不出来。9岁的孙儿黄智豪记得,“那几天和姑姑累得要死,照顾爷爷。过好一阵子才不吐了。” 常规的拍摄要求,还有划筏子等动作,但也没有照片上看起来轻松。 尽管漓江的河道从家门向前蜿蜒出很长,但撑筏子的渔翁们只能在浅水的岸边停泊,“大码头和转弯处不行”。最累的是从岸边撑出划着筏子在江上来来回回。在客人的要求下,黄全德要保持重心平衡,让筏子平稳滑动。 渔翁剪影成游客美好回忆 为了赶六点日出的好景,黄全德清晨四点半就要开始撑排。带上手电探照灯,三公里的水路,他差不多要划一个小时。“以前年轻,40分钟就撑到了。” 江面很大,竹排很长,弓腰驼背的黄全德坐在排头,披上蓑衣、斗笠,看起来很小。过去打渔累了,一肩蓑衣垫在地上躺一会,现在岸上的镜头随时按下快门,他只好坐在排头歇息。午间日头足,累了他就回去做顿饭吃,但总要再划出去赶日落。 虽然在别人的镜头里出现了很多次,黄全德不会用相机,倒是学会了看光线和角度。“夏天日头靠到(江面)落下去,就六点多那二十分钟,天上红,江上青蓝色,那时候最好看。” 渔翁的剪影伴随着撒网、喂鱼鹰的动作和点点渔灯,成为游行桂林的客人一个美丽回忆。 冬天有人找他拍也接。“大老远过来不容易。”他穿着棉衣棉袄,外面加个蓑衣、戴斗笠就出门了。碰上下雨,斗笠湿得沉,只有70斤的黄全德也能把持住。在一旁的女儿说,“爸爸很能干的”。 摄影师拍完之后,有些就走了没再联系,老人平静地说,“好少的”。拍摄他的作品获了奖,也并不知道。 但有的人找过他拍照,会依然停留在他们的记忆里。采访期间,有个女学生,两年前认识黄全德,这次在兴坪寻找了四天,终于找到老人,兴奋地拍下一组美颜照。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有些惶惑和疲惫,但也欣然。 一天下来,客人带走了回忆,他带回一天的工钱和一堆塑料瓶。临江而建的小屋,门口已经堆满了塑料制品和几百个瓶瓶罐罐。 爷孙同筏乐趣多 在孙儿看来,天天做重复的事“并不无聊”,“有时拍爷爷,有时候拍我。” 随行拍照的孙儿不怕江上风浪,“有爷爷在”。他学着爷爷模样,“爷爷把住桨,双腿张开,稳住重心,还是稳稳地站在筏子上。” “要是没控制好,一个浪头打过来,就会像我一样掉河里。”孙儿说着一头扎进水里。黄全德脸上的皱纹很深,只有在小孙儿玩耍的时候,他才像个老小孩似的笑起来,胡子一颤一颤的。 “希望爷爷一直做这个吗?”孙子不解地说,“我爷爷这身体,天天划,哪不适应。”但他也低着声,一字一顿地说“心疼”。 黄全德的老伴也84岁了,身体不太好,血压高,站起来还要拄拐杖。撑筏子回来的时间不固定,黄全德常常自己做饭。有时候儿女们过来帮忙。谈起父亲,女儿烧着柴火说,“80来岁还要劳动,不好意思了。” 她也想父亲能轻松点。“钱不够自己挣一点,还要看点小毛病。好在做几个小时就回来,不像以前做一天。” 黄全德没有用现在更轻松的电动筏子。“一贯用竹子,要到临川、兴安这些地方才能找到。以前买排子多块,现在要一千多块。”用不到一年,每年都要换新。 喂鱼鹰也是活,两只要三千来块。黄全德不懂竞争,过去常教新人喂养鱼鹰。“现在的鱼鹰一岁多,没有病就能活十年八年,一只可以养活一家七八个人吃饭。” 问到孙子将来想不想划船,他很干脆地说,“不开”,爷爷笑着说,“要大学毕业,像哥哥一样去上海。”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13801256026.com/pgyy/pgyy/1207.html |
当前位置: 阳朔县 >一张竹筏一张网划过漓江八十年
时间:2022/8/17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遇龙河边邂逅最美乡村家家户户花园洋房无愧
- 下一篇文章: 阳朔废弃糖厂改造后爆红如何在乡村打造新文
- 热点内容
-
- 没有热点文章
- 推荐文章
-
- 没有推荐文章